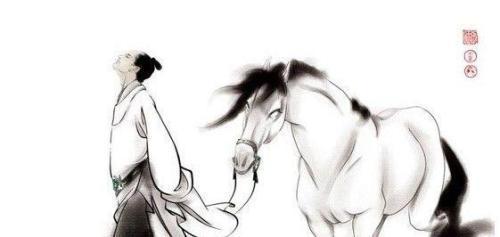 掌 灯 林晴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 一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那一年的暮秋。窗外竖着一大片竹林,早已经干枯发了黄,我笼着袖子在萧瑟的寒风中立着,感觉自己像一片正飘荡着的细长纤瘦竹叶,恍恍惚惚地从竹上落下来,不知要归去何处——也许化为尘土,腐烂在地上,一辈子隐匿在黑暗里不见天日。 他在不远处看着我。他身上还穿着衮服,厚重华丽层层堆叠,衮服的下摆在土地上扫着,沾了一层黄色的灰。他没让侍从近身,自己独行来见我,腰间挂着把镶满钻石的天子剑,一双乌黑的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咧开嘴,歪着头对我笑。我看见他的薄唇在一张一合,耳畔的声音从很远处传来。 “上次朕见你已经是一年前了。”他微笑着跟我说。我不敢看他,只垂眼看着脚下一小片被踩碎的枯叶。风刮得满天满地,整个竹林都在风中抖动,大片大片的枯黄。 我终究没有抬头。 我怕他的眼睛。 二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恐惧了。起初我以为那是孩子的梦魇,后来发现不是,这种恐惧并没有随着我年岁增长而改变,反而日渐更甚。从我懂事起父亲喜欢抱着我坐在他腿上逗我玩,我却不敢笑,因为我看见他就直直地立在不远处,用他那乌黑的眼睛看着我。 我害怕,于是我拼命嚎哭,往父亲的怀里钻。父亲用他那布满茧子的、温厚的手抚摸我的后脑勺,然后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他,笑道:“你太凶了,把你弟弟吓哭了。” 他那是不过也就六七岁光景,面无表情地一垂眼,像个成年人一般对父亲行礼,然后默默地告退。我依旧哭个没完,父亲拍拍我的发顶,“他是你哥哥,不要怕。” 我那时懵懂,尚未完全明白“哥哥”这个词的含义,问:“哥哥是什么?” “哥哥和我一样,也和你娘一样。”父亲对我道,“都是你最亲的人。” “真的?”我停了哭声。未来得及收住的滚烫眼泪顺着我的脸划过一道灼热的痕迹。然后我才知道我其实不止他一个哥哥,我有三个这所谓的“哥哥”,按顺序来,他好像排在第二位。另外两位我都不怕,一个对我温和纵容,另一个很会闹腾,不怎么理我。可我唯独怕他。 我怕他八成因为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黑很黑,像没有母亲的黑夜,望不到边际,其中也许藏着什么吃人的怪兽。我问:“全天下的哥哥,都不会伤人的吗?” 父亲被我问得顿住了。很久以后他才回答:“不一定。但你的哥哥不会这样。”他掌心的温度源源不断地传过来,直到很多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他的那只手——温暖的手,沾染过无数人的血,好人的血和坏人的血,所有在他手中殒命的人的哭魂灵加起来,足以构成一片哀鸿遍野的乱葬岗。那都是后来的事情。父亲把我交给奶娘让她抱着我回去,我趴在奶娘瘦小的肩头,望着远远有身穿铠甲的很多人向我父亲走过去,而我听不懂他们的交谈。 后来两三年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大抵是我的第一个哥哥——那永远温声细语地说话、纵容我的哥哥死在某个地方。可我所惧怕的那一个——我的二哥却没有死。他只有十岁,一个人骑着马在乱军中居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自己的命。 父亲回来以后恸哭了整整一天,哭得撕心裂肺肝胆俱裂。全军上下都穿着惨白的衣服。 我听别人说父亲并不是在为我那死去的大哥而哭,而是为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将军。告诉我这话的人是我父亲的一个军师,我从小就认识他,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总会很友好地对我笑。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酒气,长得也好看,从来不束发。我挺愿意他去当我的哥哥的,但他却只叫我四公子,对我的态度亲切却又疏离。 我不信。我问:“父亲难道不喜欢大哥吗?” “他当然喜欢。”军师笑着看着我,压低了声音,“他是在演戏呢。” 我睁大眼睛。他用食指在唇前竖了一下,示意我不要把这话说与旁人听。 于是我不敢问了。那个下午我听闻军中有人传话,说我的二哥是天生的好命,不仅大难不死,还将必有后福。我的大哥死了,他成了我的大哥,但我不习惯。我只会唤他二哥,从我五岁唤到了我三十五岁。 唤到他死的那一年为止。 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写文章。父亲为我找了很多夫子,一天到晚地陪我坐在书房里给我讲课。我迷上了墨的味道——那黑色的液体,虽然也是黑沉沉的,像二哥可怕的眼睛,却和后者有本质的区别。我拎着墨迹未干的新诗去给父亲看,父亲尚未说什么,一边的官员却要夸了:“四公子小小年纪文采盖世,以后必将成为国之栋梁啊。” 我期待地看向父亲。父亲大笑,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来的几年是我在书卷中度过的。我听着父亲战胜了战败了的消息交替传过来,那笑眯眯的军师不知什么时候也不在了,就这样一天天地在我的诗歌里,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渐渐拉长,心却在渐渐变老。父亲越来越喜欢我,随着父亲对我的好感飞快增加,我对二哥的恐惧也逐渐减退,到最后已经变成了麻木。他从来不和我主动说话,偶尔说的也都是些场面话,就像父亲当年“演戏”那样。我逐渐地意识到,人长大到一定岁数,就不得不开始演戏了。 演戏的步骤并不复杂,只要在公开宴会上我们两个对着行礼,互相让菜,再问问对方身体情况,微笑着聊天给周围人看,塑造出一副兄友弟恭的假象就好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很多事情,知道这天下是乱的,父亲是乱世之中的王。我知道南方有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对我们虎视眈眈,他们两个曾经联手过,让我父亲很是狼狈。 我依旧怕着我的二哥。他的对我的态度随着年岁增长一直模糊不清。我永远不知道他究竟是想无视我,还是想除掉我。一个夜里他请我到他房中喝酒,我以为例行的演戏又要开始了,端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去,却不见本该来当观众的旁人。只有他一个人等着我,在金色的宫殿里,在与外面浓稠夜色隔绝的雕梁画栋里坐着。他面前只有一个低矮的案子,案子上放着两杯酒。 我过去坐下,垂眸去看倒映在酒面上的我自己。他没看我,自顾自地斟酒,然后平平淡淡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说话。” 我嗯了一声,扬起笑容:“能和二哥坐在这里,真是……” “不必如此。”他抬手制止我。“我知道你怕。” 我沉默了。 “你一直怕我?”二哥晃着杯中的酒液,液体里沉浸了一片细碎的光斑,是周围烛光溶解在了里面。烛光在抖,酒面也在抖,让这画面变得光影迷离。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缓缓地抬了头,又一次真正地直视他的眼睛——深不见底的眼睛。那一瞬间我像是堕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深渊,飘飘荡荡地坠落,看不见尽头,只能看见头顶上迷蒙的天光。 “怕我杀你。怕我给你下毒。”他指指我面前的酒杯,我仍然茫然地看着他。过了很久我才顺着他的手指讲视线转移到我眼下的酒杯上,同样浸着烛光,却分外平静。 “父亲说过,哥哥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之一。”他又道,这一次竟然微笑了。我看着他的微笑,突然觉得心脏里某个东西嘎达一声松动,紧接着整个人都要栽下去。我颤抖着声音开口:“二哥,你……” 这么多年前的话竟然记得一清二楚。他那一年才六七岁,父亲随口一言,他记了十几年。 不过这当然不是重点。我猛的拿起酒杯给自己灌了下去,因为恐惧,不少酒液进了我的鼻腔和我的领口。我又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看着他脸上那两个恐怖的乌黑的深渊底部透露着出一丝丝诡异的笑意。我再一次不敢看他了,匆忙用袖子擦干脸上的酒,起身仓皇地往大殿外走,几次几乎摔倒在地上。他在后面坐着,也不拦我,只是饶有兴味地看着,任凭我慌张地闯进黑夜里去。 “四弟!”等我跑了很远以后,我听见他在我身后笑着大喊。“天黑,莫忘掌灯————” 四 那一天终于来了。 父亲死的那一天,哥哥登上皇位的那一天。 我被人抓进了皇城,带进皇宫大殿扔到他面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着衮服,脸上的神色被冠前缀下来的珠子掩盖在后面的模样。念完最后那句诗,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母亲抓着他的袖子,哭得脸上的胭脂都晕染开来,她在朝他尖利地嘶吼: “那是你弟弟!你要敢害你弟弟,就先从你母亲的身体上踏过去!你个逆子!你个畜……” 他还是面无表情的,像一个冰冷的雕塑。我念完那句诗很久之后还泣不成声,也不敢擦我的眼泪,感觉我的心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大殿上的空气几乎静止,很久以后,当我几乎感觉是在做梦的时候,我听见他在高高的金殿上对我平静地说: “回雍丘去罢。做你的王。” 我腿一软要跪下去,膝盖还没有触地,被一左一右两个侍卫捞了起来往殿外拖。我耳畔仍然环绕着母亲哭骂的声音,群臣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殿外呼啸的风声。在那些声音里,我是一个游戏的失败者,现在付出该付出的代价,但也是我最好的结果。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无比肯定地跟我说,若我不改了我的性子,我的二哥迟早会变成剁碎我这块鱼肉的刀。我当然改不了——我对他道,就算我改了,只要我还是他的四弟,有些东西一辈子都终结不了。 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进过皇宫的大门。三年后我乘车过了那条浩荡的洛川,车子摇摇摆摆,我靠在窗边撩开帘子,把目光投向那水雾迷蒙的江面。恍惚间我看见一个极为美丽的妙龄女子行走在江上的雾气之中,远远地冲我一笑。我失了神,问身边的侍卫:“那江上可有人站着?” “殿下说笑。”侍卫忍俊不禁,“人怎么可能站在江面上。是殿下眼花了。” 但我确信我看见了那个女子。她的身影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趁车马歇息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到川边漫步眺望。川上的风是湿冷的,我的衣服被空气缓慢地浸湿,洛水在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岸边的芝草在随着风轻轻摆动。我闭上眼睛,于黑暗之中却仍见洛水,仍见那曼妙女子立在水上。她身着华美的服饰,面对着我,明亮的眼睛中溢出温和的水波来。 于幻想中我问她:“你可就是洛神?” 她微微颔首低笑。裙下游鱼的鳞片闪烁着变幻的光,远处传来了神明缓缓的歌声。我解下玉佩走向她,她却转过身去,为我留下一个烟波浩渺的背影。风大了,水雾渐渐腾起,于我二人之间形成了一层天然的帘幕。这时候我听见她说:“人神道殊。” 我错愕,不知她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她没有回头,慢慢地行于水上走远。无边无际的乳白色冷雾温柔地包裹住她的背影,她消失在了川流尽头。 我突然想到,人神道殊,而人与人本该同路。 我原先怕那个人怕的要死,现在才发现,其实,我原本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只不过后来才渐行渐远。而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本以为我从最开始就和他不是一路人。如今想走回去,却发现身后的路已经消失了,再也找不见。 五 他死了。 他死时正是冬天,雨水淅沥沥地下。我没有想过他竟然会比我死得还早。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深深地坚信总有一天我会被我这可怕是二哥折磨致死,只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死,他就先一步合上了眼睛。 勉勉强强在人世走了不到四十载,当皇帝当了七年,算是解脱,以后不必再演戏。这些年我养成了每天写文章的习惯,在每一篇文章开头都会记录今日的日期。今天我又习惯性地写下他的年号,顿了一下,才想起来他的儿子已经登基,如今又是新的元年。不过我没有把那两个字涂去,径直在后面又写下了“八年”。 不存在的第八年,正月雨。 窗外的雨水连绵不断,带着寒冬刺骨的寒意,那片枯死的竹林在雨中挣扎着摇晃,叶子已经落尽了,被打成了深色,软绵绵地贴在地上。 在那片竹林里他曾经见过我。我记得他的模样,依旧是乌黑的眼睛,手里握着那权贵的剑,微笑着唤我。“四弟。” “臣在。” “还记得朕对你说过的话吗?”他问,深不见底的眼睛又望向了我。“朕请你喝酒的那次。” “记得。”我终究没有抬头,盯着脚下卷边的枯竹叶。“臣夜里出门,一直是带着灯的。” 那昏黄的光——漫漫黑夜里唯一的光源。有时候我看着那把灯,能把自己看出错觉来。我从灯里能看见熟悉的人的面影,看见一些过去的岁月,看到父亲母亲和死去的大哥,甚至能依稀辨认出几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他依旧微笑着看着我,道:“那就好。雍丘不比皇庭,夜色要浓些。” 我沉默不语。 “路也不好走,可要看清楚了。”他继续道,说完这句话,他缓慢地转过身去,留给予我一个秋风萧瑟里的背影。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再一次回到国都,竟然是为他去奔丧。在那里的人群中我穿着素白的衣服,站在队伍里听远处祭天者凄惨缥缈的哭泣声。丧礼过后已是深夜,我一个人磕磕绊绊地沿着宫里参差的台阶往外行走,侍卫备着马车在外面等我。 上马车之前我再一次回头看向黑夜中宏伟的宫殿,远处建筑的轮廓被吞没在冷风里,脊兽似在低低地悲鸣。从当初他在雍丘竹林见我的时候我就想问他一句话,如今没有机会了,只能现在默默地在心中问他的灵。 你,可是我的二哥啊。 如果我的灯没了,我又要到哪里去找呢? 指导老师:李晓甜 【点评】 这篇文章可以看成一篇小说。用曹植的口吻,叙述了“我”和曹丕二人之间的恩怨。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可以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刻画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事件。这种写作,一方面需要对历史知识有准确、深入的了解,洞悉人物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要有丰富、细腻的想象与联想能力,能将历史记载中粗疏、简陋的部分补充得细腻、充盈。对于中学生的写作训练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本文在上述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秀。不过,文章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情节的设计并不自然,例如“掌灯”这个标题,在文中的呼应不够清楚自然;洛神的出现也比较突兀,看不出真正的内涵。小说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说不上立体,从历史上看,曹丕应该不只是一个“眼睛乌黑”的野心家,而曹植也绝不是像文中所表现的那样懦弱。 (责任编辑:admin) |
